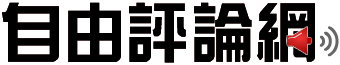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在面對強權壓迫、集體創傷經驗、以及尋求集體治癒的過程中,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差異?
《少年來了》(2014)是以韓國光州事件為主軸的小說,作者是以《素食者》獲得2016年國際曼布克獎的韓國作者韓江。這本書出版之後得到很大的迴響,在韓國銷售超過廿多萬冊,2014年獲得韓國「萬海文學獎」,2016年被英國衛報評為年度選書、愛爾蘭時報年度最佳小說,2017年獲義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Malaparte Prize)、2017年美國Amazon書店百大選書等。

身為作家,韓江每當執筆寫作時,都會思考自己究竟為什麼會對人性存有這麼多疑惑,隨著她的持續寫作,這個問題變得更加鮮明。多年來她在創作過程中不斷探討人類的暴力與慾望,試圖拼湊起對自己疑問的完整答案。最終,出身自光州的韓江決定正視那段光州記憶,重新拼湊起關於那起事件的種種片段,於是以父親的學生東浩為主角開始蒐集資料、訪問生還者後寫下這本小說。
《少年來了》的敘事跟其他敘事有何不同?
與大部分討論光州事件及其他類似事件論述的不同處在於,在這本書裡,少年及女性佔了敘事主體的大部分,她/他們雖然無力,卻仍勇敢地面向強大的壓迫者,並在殘忍的暴力壓迫之下,受到延續多年的巨大創傷。
1980年5月,韓國光州市民與學生組織示威遊行反抗全斗煥政權,其後政府軍開始了一連串的血腥鎮壓。書中並沒有太多討論到當時的獨裁政權領導者全斗煥、以及由成年男性組成並執行血腥鎮壓任務的政府戒嚴軍。書中登場的人物有正在讀中學的少年們、自願來道廳尚武館協助處理遺體入殮的女高中生、年輕的工廠女工、以及死去少年的母親。
《少年來了》書中雖然也談到在民主化運動中最常被提到的男大學生,但更多是以當時參與或涉入的女性為主體,這些女性往往在光州事件之後以成年男性為主體的家國敘事中被忽略。
性別與記憶
為什麼要強調女性?因為這對我們該如何面對過去集體創傷的記憶與經驗極為重要。忽略了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經歷,我們就無法正確、完整地面對過去。
有次跟韓國朋友們一起閱讀、討論這本書,我們都同意《少年來了》書中出現的人們,就像是我們每天會碰上的隔壁鄰居,是真實在日常生活裡常會遇上的人物。他們其實跟我們一樣,都是面對危險會害怕、面對困難會想躲避的平凡人,只是覺得自己應該要站出來的道德良知,讓他們因此而做出許多勇敢不凡的抉擇。
這些平凡人和我們看好萊塢或是韓國英雄電影裡的主角很不一樣,他們都是平凡人,柔弱而無力,沒有任何特別的地位或才能,也沒有超能力或武功來保護自己、藉以行俠仗義。就像死去的少年一樣,雖然害怕,卻仍以肉身去抵擋槍砲,犧牲自己生命的結果,也並沒有因此而拯救了世界。
這樣的論述方式,其實跟許多相關事件的文字或影像的敘事形成對比。最大的差異,也許在於社會對男性陽剛特質所期待並賦予的侵略性。
以2007年的電影《挖角》為例,這部電影講到某位球探回到故鄉光州,準備挖角一位實力超強的棒球投手時,剛好遇上光州事件發生的那九夜十日故事。球探遇上昔日的初戀情人,一起看著出現在電視上的獨裁者全斗煥時,球探對著昔日情人說:全斗煥是「真正的男人」,跟妳們搞民主運動的人不一樣。當社會裡擁有話語權的人主要是男性,而男性又被期待具有侵略性的陽剛特質時,暴力常常就被美化成為達到社會秩序所需要的工具。
不只壓迫者這樣覺得,有時候連挺身反抗壓迫者也會如此,過度強調陽剛特質而忽略了不同的參與者與看事情的角度。在讀完《少年來了》之後,我再度回想過去看過的、關於光州事件的電影《華麗的假期》。劇中女主角的父親曾是特勤軍上校,在戒嚴軍即將進入光州之際,號召了一群男性組織起人民軍。他對著男性群眾演說,說那些戒嚴軍已經褻瀆做為軍人的榮譽,不配做為國家的軍人。因此,大家要拿起槍、團結起來,做為男人對男人、軍隊對軍隊進行對抗。為了安全,女主角被送離人民軍據守的道廳(政府大樓),也因此在痛失戰死的父親與愛人後,成為悲傷孤獨的遺族。
然而,在真實的光州事件裡,女性從未自與戒嚴軍正面對決的道廳裡撤守。不管是在裡面擔任總務工作、或甚至是拿起槍來參與戰鬥,女性並沒有逃離反抗的現場。《少年來了》裡面,談到許多女性自願留在道廳,後來因此被殺、被逮補、被強姦虐待等遭遇。這些真實的過程,卻長久被掩蓋埋沒在以男性陽剛為主的論述裡。女性不只一起參與了行動,也一起遭受到迫害。即使是那些留守在後方的女性們,也一樣參與了這樣的過程。就像《少年來了》書中,死去少年的母親,在往後的歲月中承受了無盡的創傷與悲慟。
性別的差異對於我們所擁有的集體記憶影響非常大。首先是說話者的性別,不同的性別,對於如何形塑出關於創傷的反應與論述,存在著顯著差異。身為女性的韓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不同於男性觀點的故事。那些挺身而出的女性、以及身為被殺害或被視為罪犯人士的妻子、女兒、母親的婦女們的苦難,也必須受到正視。當男性受難者被視為國家英雄的時候,這些承受更長久苦難的遺族女性們,也必須得到該有的尊重。身為女性的韓江,為這些共同承擔苦難、卻常被遺忘的女性們,寫出了她們微弱的聲音。正是這些溫柔的聲音,讓讀者們找到了共感,許多人讀到死去少年母親的心聲時,因此而泣不成聲。韓江的這本書,因此被形容成安慰並洗滌死去靈魂的一種儀式(씻김굿)。
關於創傷與醫治
陳香君在《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這本書裡,談到創傷的特性。創傷永遠存在於當下,因為它絕不會經由敘事而成為過去的記憶。受創的人,很多時候生命就停留在那一瞬間,只是事件發生的當下,人們根本就無從得知自己已經受傷。然而,當某個間接事件再次觸發這樁創傷事件的某些相關事物時,這個不得而知又不復記憶的事件,就會以某種替代形式回來。因此,受創的過去永遠不會消逝,而是留下來,在無法預期的時刻,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傷口還在。最後,創傷是可以傳遞的,而且能代代相傳。即使對於未曾經歷父母過去的孩子,也會感受並繼承父母曾受到過的創傷。焦慮、驚恐、羞愧、罪惡感、極端的苦痛,無論是身體的或心理的,這些都可以壓垮這些受創者心靈。
真實面對過去創傷,並且承認不同受創者的經驗差異,是醫治這些創傷的必經過程。就像韓江一樣,她雖然未曾直接經歷光州事件帶來的壓迫與創傷,卻無意識地承受了父母親輩所受到的壓迫、傷痛,讓她對人性從此多疑、無法輕易信任。然而,只有正面對決過去的經歷,才有可能醫治那長久來的傷痛。而讓共同參與這些受創過程的女性,能有更多機會與空間,說出屬於她們自己的經歷與感受,才是讓集體創傷能早日治癒的過程與方式。因為男性與女性共同承擔了那些傷痛,我們也因此必須共同進行醫治的過程。
我想到一位男性友人曾對我說過自己當兵的經歷。他曾被派到偏遠離島上當砲兵,而那是他多年後至今仍不願回憶的黑暗記憶。他形容著,每次要經過那長達三、四百公尺的黑暗隧道,到海岸邊的砲台值勤時,心中總是充滿著恐懼。軍隊中強調男性陽剛的特質,霸凌是每天常見的事,常常有人「無意間墜海」、或是「跳海自殺」,在漫長黑暗的隧道裡,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情,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活著走出去。
不知為何,這段話讓我很難忘記。讓女性重新回到該有的位置,並受到該有的尊重,其實受益的不會只是女性。
回到最初的問題:在面對強權壓迫、集體創傷經驗、以及尋求集體治癒的過程中,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差異?答案是:是、也不是。我們的確因著自己不同的性別,而存在著不同的受壓迫與受創經驗,正如身為女性的我,不用去當兵、不需承受那些軍隊裡的黑暗面。然而,不管男性或女性,大多數的人,都一樣會受到權力的壓迫,甚至因而受到創傷。不管身為男性或女性,幫助彼此能說出該說的話、回到該有的位置、得到該有的榮譽與肯定,其實,就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參考資料:
陳香君 《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典藏藝術家庭,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