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直很好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心理治療究竟如何進行。畢竟近代心理治療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的產物,多數心理治療也帶有鮮明的文化特徵。特定心理治療離開其所屬階級、文化的同溫層,若非窒礙難行,必然也有許多轉折變化。特別是在殖民這樣的權力結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於治療中如何交談,各自又如何看待、詮釋彼此的交會,其實有不少值得玩味之處。因此,自多年前得知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精神醫學教授中脩三曾於台灣推行森田療法後,就一直希望能找到相關記載,但一直到最近才在其所成立之「日本精神療法醫學會」於1945年2月發行的《心理と医学》第三號中,發現一段他所摘錄的本島青年心理治療記錄。這份記錄相當簡短,而且中脩三在戰爭時期選擇將其公開,其實有為官方政策與意識形態宣傳的目的,但作為可能是台灣最早的心理治療記錄,還是值得分享,並加上若干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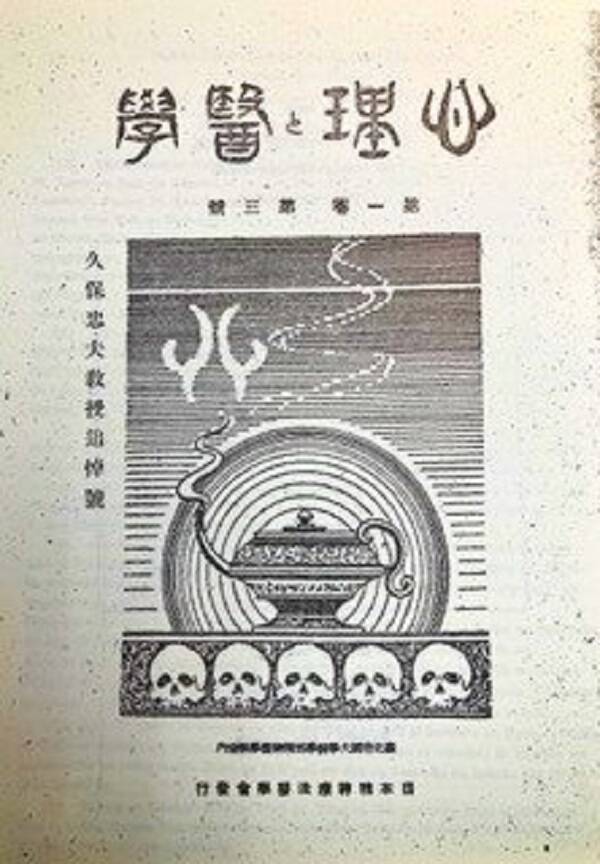 圖1 《心理と医学》(來源:《精神障害者問題資料集成・戰前編》,第12卷)
圖1 《心理と医学》(來源:《精神障害者問題資料集成・戰前編》,第12卷)
森田療法
首先,有必要簡要介紹森田療法,以及中脩三在台灣推行森田療法的背景。森田療法是日本精神科醫師森田正馬(1874–1938)於1910年代晚期發明、針對神經質性格患者的住院心理治療法。森田認為當時日本流行的神經衰弱並不是一種神經或身體疾病,而純然是由於神經質性格者的心理作用所致。森田所謂的「神經質」,乃是一種生來的內向性氣質或性格,其特徵為高度的慮病焦慮,以及強烈的自我意識與完美主義傾向。神經質者的「神經衰弱症狀」,事實上乃是一些正常的自然身心變化,但他們因為過度擔憂而不斷注意,以致提高了對這些變化的感受性,陷入注意與感受性相互加乘的「精神交互作用」惡性循環中,從而延續且增強了這些「症狀」。森田強調神經質者的慮病(死亡)恐懼,乃是其強烈自我(生存)慾望的反映,其為自己設立了不切實際的理想,以致陷入不斷自我檢視、自我懷疑的強迫性焦慮中。其創設的森田療法,除了治療症狀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則是要鍛鍊陶冶神經質者的性格,使其能發揮性格上的優點。森田療法分為四個階段:(1)臥褥療法期,(2)輕作業療法期,(3)重作業療法期,(4)實際複雜生活期,每個階段各約一週左右;此外,從第二階段開始,被治療者每日都要撰寫日記,記錄每日工作點滴與自己的感受體悟,交由治療者批閱指導(中脩三發表的記錄,即是患者的日記與他的批示。)森田療法的要旨,在於引導被治療者在自發性的工作中,體會自己強烈的生存慾望,了解慾望與焦慮實為一體兩面,並培養融入現實世界以在其中追求實現自我的生活態度。
森田的神經質理論與療法在戰前日本得到相當的共鳴。對於當時日本的中產階級而言,面對資本主義階層化與工業化的工作體制,森田提供了一種工作與人生哲學,使他們能在「柔順」與「自主」,以及在「適應環境」與「自我實現」之間達成某種平衡,而得以適應當代工作環境又不至喪失自我價值。雖然當時日本精神醫學受德國精神醫學影響主要採取生物精神醫學取向,一般並不重視心理治療,森田療法也得到若干精神科醫師認可。特別是九州帝大精神醫學教授下田光造(1885–1978),他稱許森田療法為日本的偉大發明,是可以與精神分析等西方心理治療相提並論的東方心理治療法,並在九大精神病房施行森田療法。然而,下田也就森田理論作出一些修正,而更強調神經質性格中的「劣等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並主張神經質性格成因除了先天體質外,後天環境也扮演重要角色,而日本嚴格的家庭教養方式正是製造神經質性格的溫床。
1934年來台就任養神院醫長的中脩三(1900–1988)即是出身九大精神科。受其老師下田光造的影響,中脩三也嘗試在台灣推行森田療法。不僅如此,中脩三還強調心理治療在殖民地治理與帝國擴張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他將「對於異民族施行心理治療的效果研究」列為台北帝大精神科的研究願景,主張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必須以對異民族的心理治療為基礎,認為只有「心理治療可以真正實現心與心的溝通」,必須「從民族融合的角度開始進行心理治療」。此外,他還認為「大東亞的建設在於民族間真正的相互理解」,而從事心理治療醫師的使命即在於「個人的、直接的增進此理解」。這是中脩三在台灣推行森田療法的背景與宗旨。本文所分享的記錄,以時間推算,應是他剛到台灣時最早進行心理治療的本島人個案之一。理想上,下田光造所強調的後天環境與劣等情結,若能適當應用,或許也是理解殖民體制如何影響被殖民者心理的有用概念。
但現實總是比較複雜一些。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中脩三於1945年提到這是十年前的記錄,而日記是從五月一日開始,換言之,這位患者應是在1935年四月底住入養神院,經過約一週的隔離與臥床休息後,於五月一日進入第二階段的輕作業療法。這位當時25歲的個案(以下稱為A君)為台北高等學校學生,但已因病休學一年以上。從日記記載看來,A君家境應該頗為富裕,父親為土木工程包商,家中有廣達近九千坪(三甲步)的花園,當年春天才新植了「四百株的杜鵑」與「兩百株最新種的洋薔薇」。依A君所述,其成長過程「自小與內地人共同生活交際」,因此其或許是就讀小學校而非公學校,而後他進入台北工業學校土木科就讀,畢業後通過激烈升學競爭考入當時台灣接受大學教育的唯一管道-台北高等學校。無疑的,A君可以稱得上是本島青年中的菁英。
A君所患的病為神經衰弱,或至少他的自我診斷為神經衰弱(以中脩三在台灣所用的診斷分類,A君的正式診斷可能是「心氣症」,而「心氣症」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視為是森田「神經質」的同義詞。)在五月一、二日前兩天的日記中,A君提到他當下的心境「既無怨恨,也無羨慕嫉妒」,但是他認為這種帶著感傷的平靜,並不是真如「明鏡止水」般的平靜,而只是「神經衰弱患者常見的在興奮後的病態沉靜狀態」。A君提出許多問題請教中脩三,包括自己低落的「食慾、讀書慾、性慾、活動慾」是否能夠恢復;康復後是否能夠復學,還是應該斷念大學教育返回鄉里務農;以及腸胃功能不佳應如何治療等。其中,性慾似乎是A君一個主要焦慮。他提到自己有精液洩漏的困擾,小便有時混雜精液,擔心像精液這般「一滴等於數百滴血液的貴重東西」如此流失下去,會讓身心衰弱更為嚴重,他從書中得知此問題可以「電氣療法」與「水浴」治療,不知中脩三是否贊成。此外,他還提及因為性慾不振,去年起曾接受近五十次的賀爾蒙注射治療,卻不見效,他擔心自己這樣今年冬天是否適合結婚,而婚後若生育,子女是否會遺傳自己病態而低能或發育不良。
依照森田理論,A君這些症狀與擔憂,都是神經質的典型表現。因為其慮病傾向,神經質者會過度注意精液洩漏或快感缺乏(anhedonia)等在正常狀況下也會偶然發生的身心現象,他們追求完美而不斷自我檢視,以致延續並放大了這些症狀。治療上,在森田療法中,治療者通常不會就這些症狀多作討論。其理在於神經質者必須學習如實接受這些身心現象,他們不應一直觀察或嘗試去改善或消除它們,而應將注意力投注在具體工作上,即使感覺缺乏動力,也應繼續工作,如此自然會感受工作慾望由內而生,從而領悟先前造成困擾的症狀都只是出於心理作用。因此,中脩三對於這兩天的日記只有很簡短的批示,告知A君精神若是健全腸胃自會健康,不需服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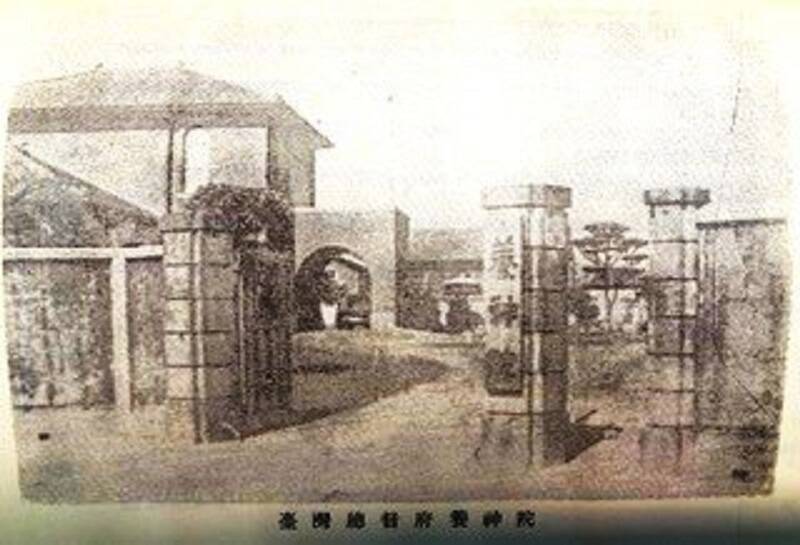 圖4 養神院(來源:《台灣總督府養神院年報・昭和九、十年度》)
圖4 養神院(來源:《台灣總督府養神院年報・昭和九、十年度》)
真、善、美與「純心」
而後幾天,A君陸續在日記裡抒發不滿。先是五月三日A君見到某位內地人事務員斥罵一位本島人工友,感到十分憤怒,差點忍不住與他發生衝突。A君憤恨自己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情,被這位「教養低劣」、「月薪最高只有五、六十園」的「下級官吏」打亂;還說以這位事務員赤裸裸「內臺差別」的表現,難怪部份本島人會感到憤慨。A君提到在台灣,許多下級官吏都是在內地所謂「生存競爭」中敗北,無法稱心如意的生活才渡臺,但他們卻通常缺乏同情心,而有特別強烈的「內臺差別」傾向。對此,A君說自己基於正義感,實在難以正視。他問中脩三:「這是社會的實狀嗎?還是自己太神經過敏?」中脩三的回覆則是:「不拘束。在任何地方都應作自己的主人(隨所為主)。為了東洋民族,成為一個有為的青年。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接著,在五月五日的日記裡,A君抱怨病房太過狹小擁擠,且從入院以來,不知是因為食物或飲水,他一直拉肚子,在這樣的環境裡,他無法遏抑空想,對什麼工作都提不起興趣。他覺得住院只是如「矯角殺牛」般的無謂之舉,想要出院在有著廣闊花園的故鄉療養,如此他的「神經質」必能瞬間消失。對此,中脩三的回覆勸誡A君不應追求如「心情愉悅」、「美」或「輕鬆自在」這樣的感受,警告A君現在對於故鄉快樂生活的想像,就是他將來於故鄉再發病的原因。他鼓勵A君若有鍛鍊修養自己的志向,就會覺得這狹小的醫院是神殿,而只有能夠不受環境影響,將來神經衰弱才不會再復發。
大體上,中脩三此處回覆也符合森田療法的精神。森田正馬指出神經質者經常為「氣分本位」,執著於追求如「愉悅」、「輕鬆」等想像的感受,卻不知情緒乃依情境而生,隨時變動不居,以致深感苦惱。森田教導神經質者必須培養「事實本位」的態度,應了解並接受自己心情會隨情境流轉變化的事實,如此才能不受情緒影響,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融入當下情境,在真實工作中實現自我。
中脩三的回覆似乎打動了A君。在隔天的日記裡,A君提到讀了中脩三的批示後,感受到許久未曾有過的平靜,也不再覺得醫院生活如此難熬,甚至還希望接下來一、兩週的住院生活可以更艱困一些。他稱讚中脩三的教誨宛如聖賢之言,覺得內心任何痛苦都可以向中脩三訴說。但是A君對於中脩三說不應追求「美」感到有些疑惑。他提到高校「修身」課本教導人類一切文化活動都在於追求真、善、美,以追求真、善、美為至高無上的目的,而這也是他人生的目標。A君說他不想過虛偽的生活,也懷疑所謂「社會游泳術」這樣的處世法的價值。他回憶起休學這一年來在家鄉的經驗,他覺得自己就好像是個「社會人」一樣,常常裝模作樣,明明不開心也假裝高興。他很懷念自己在高校時自尊心強、意氣軒昂的樣子,擔心自己再這樣下去,很快就會變得像他所看不起的俗人一樣了。A君說耶穌與托爾斯泰所宣揚的「絕對無抵抗主義」在現世已經行不通了,他無論如何也想過有個性的生活,寧死也不願意失去個性,他想要持「理直,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生活態度,問中脩三覺得如何。
對於A君的疑問,中脩三強調森田正馬所言的「純心」(純な心,素直な心)的重要。他指出人類文明的發展只是因應人口增加的需要,真、善、美並不是人為的、智識的虛妄理想,而必須從似是而非的文明論中醒悟,滅除心智,依循自然的純心,才是真正的真、善、美。他鼓勵A君時代正在改變,重視表面功夫的俗氣世界已經過去,無論如何都要依循自己與生俱來的澄淨心靈,追求純粹、真實的人生。
然而,「純心」豈是如此容易維持。不要說現實生活,即使是在心理治療這樣的私密時空中,治療者與被治療者恐怕也很難感知自己的「純心」為何。以後見之明,此時討論著真、善、美與純心的中脩三與A君,似乎仍只是在搬弄「社會游泳術」,以避免正視兩人關係的現實。
童養媳與真愛
中脩三並未摘錄A君接下來十幾天的日記,因此無從得知A君這段期間的狀況與心境變化。或許A君的精神體力已漸漸恢復,也或許他對中脩三有了更高的信任感。因為他從即將出院的五月十八日起,接連幾天寫了長篇日記述說自己困擾,希望中脩三能給他指引。當然,這也可能只是因為出院在即,這些問題有了更高的急迫性,或是A君自覺住院一無所獲,不甘心就此出院,而孤注一擲的拋出這些難題。
首先,是婚姻或者是說愛情的困擾。
在五月十八日的日記裡,A君先是沉痛的抱怨即使很了解自己、教養與自己相當的親友也無法了解自己痛苦,更何況家中未受「教養」的父兄。A君批評父兄是「生活的中毒者」,汲汲營營於世俗生活,腦中只有錢,對於他們而言,A君認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詩」,就像是給豬吃的東西一樣,若真的非得與他們共同生活,那他寧願死。
接著,A君向中脩三訴說了一直以來有所顧慮而未告訴中脩三的感情困擾。他沉重的說,身為本島人,當想要打破舊來陋習時,就勢必得先面對必須違逆父母的沉痛現實。他問中脩三是否知道本島人的童養媳習俗,並為中脩三解釋了這個他認為「完全無視人格」的習慣。原來A君家中也有一位預定將來與他結婚的養女(媳婦仔),A君自述他從十五歲開始,就一直為此問題困擾。即使A君曾想遵循前年去世母親的遺願,努力嘗試與養妹經營愛情,但因為從小一起長大,對她實在只有兄妹之情,對方應也是如此。A君說這種感覺若非親身經歷,應是無法了解。他還說自己原本就因重度神經衰弱而對人生抱持悲觀看法,若真的與養妹結婚過著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那生命就毫無意義而不值留戀了。
不僅如此,A君在休學回鄉這一年間,愛上了一位他覺得「可以隨時為他犧牲生命」的女性。A君自認這是真愛,希望與其成婚,但是受到了父親與友人以母親遺言、對不起養妹、此女只有公學校學歷不及其養妹、此女也曾是別人家童養媳等各種理由反對,父親甚至以死相逼。A君認為在父親及友人的想法裡,人生就只是「生活」而已,沒有任何理想,他無論如何都無法認同他們的意見。A君說想到自己的處境,就覺得中脩三所說的「滅卻心智」聽來有些諷刺,若自己不要進高等學校而做個「無學文盲」的農夫,應該不會有這些困擾了吧!他還說即使自己能夠體會中脩三所教導的「隨所為主」與「任憑自然」,也還是不知應該如何是好。A君覺得若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神經質應就會好個大半,他相信中脩三一定能夠不辜負他的信賴,給他正確的指引,將他從長期痛苦中解救出來。
對於A君的求助,中脩三的回覆劈頭就說A君還不具備成家資格,並警告初戀多是盲目的,絕不能一時衝動就輕率結婚。他提醒A君在這個必須自己尋找良妻的時代,最佳伴侶並非輕易可得,或許A君也尚未遇到真愛。他鼓勵A君暫時放下這個問題,對於父親要求可以先虛與偽蛇,將熱情投注在課業上,努力鍛鍊自己的人格與體力,使自己更加成熟獨立,屆時自然就會知道如何判斷。
中脩三的回覆今日讀來或許有些不合時宜,但某個程度上乃是依循森田正馬的戀愛觀。森田正馬受廚川白村暢銷書《近代戀愛觀》與有島五郎殉情事件觸發,曾著有《戀愛の心理》一書,批評廚川、有島等人所追求的「剎那的、享樂的」「戀愛至上主義」,主張不應將愛情理想化,而應慎重務實的選擇配偶,且夫妻間應互相合作尋求彼此的調和。他強調唯有這樣奠基於現實的愛情才能增進人生整體幸福,並提昇自己的人格。
然而,中脩三的回覆卻似乎觸怒了A君。這也許是因為中脩三否定了A君的愛情,或是因為他評斷A君尚不夠獨立成熟。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中脩三並未注意到A君向其訴說自己苦惱時,似乎將其當作本島青年命定的困境。他多次提到「吾等本島人青年」從小就得背負童養媳這般「本島人陋習」的枷鎖,唯恐中脩三難以理解,他還詳加解釋何謂童養媳及其不合人情之處。此外,他一再提及自己與家鄉「未受教養」親友的不同,強調自己完全無法認同他們的價值觀。因此,A君先前一直忍耐不願向中脩三吐露此事,不無可能乃是出於某種民族或文化自卑感;而他也期待中脩三可以同情理解像他這樣具理想性的本島青年所面對的無奈處境。對於懷著如此心情的A君,中脩三把他視為是受流行文化迷惑、追求戀愛至上主義的青年,想要教導他正確的戀愛觀,卻不知A君所糾結的並不只是愛情,也不只是戀愛觀層次的問題;而對於A君而言,中脩三的回覆,難免讓他有中脩三對其困境一無所知,卻擺著高傲姿態給出一些自以為是的建議的感受。
從這個角度,或許就能理解A君隔日的反彈。
台灣人意識
在五月十九日的日記裡,A君先是反駁了中脩三「初戀多是盲目的」一語。他說他在燃燒著無限知識慾的年輕時代,曾經對自然與人生充滿感觸,那時他將女性「偶像化」與「神聖化」,從女性追求詩的靈感。但是在進了高校以後,他受名譽慾驅使,每日都在圖書館中查字典閱讀西洋書籍,覺得如此生命才有價值,那時他腦中完全沒有女性的位置,覺得當初醉心文學的浪漫主義情懷幼稚可笑。然而,他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此時的他既不會將女性神聖化,也不會將之視為玩物,而他也遇見了一位願意為他犧牲生命的女性。他說他反覆思索了廚川白村的近代戀愛觀,覺得完全贊同。他還以中脩三所說「知識是迷惑之根源」一語反駁中脩三,辯說符合理想的女性並非隨處都有,人終其一生可能只能遇見一、兩次真愛,理想太高只會造成悲劇。
接著,A君筆鋒一轉,不再討論愛情問題,而突如其然的宣告他決定不再回高等學校了。他說一個人若是不注意自己腳下而盲目前進是非常危險的,而他認為接受大學教育對於本島人而言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本島人的學士,能夠去哪裡呢?」A君到即使是台北帝大,自從開辦以來本島人學士能在其中任職的也不過一、兩位,其他本島人學士只能淪為高等遊民,求職受阻,說出胸中不平還會遭白眼。他直率的問:「我們本島人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呢?」他強調自己並非在抱怨,而只是說出事實。
接著,A君又提到本島人想到憧憬已久的內地旅行時,若是乘坐汽船,「我們台灣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活人,都會不只一次被水上警察盤查目的地。」A君曾與內地人友人同行,經歷兩人間的差別待遇,覺得非常悲哀。他說自己從小與內地人一起生活社交,很少意識到自己是本島人,但是現今他「痛切的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
寫了這麼多之後,A君似乎有些不放心。在當日日記結尾,他特別聲明這些話他平常並不會隨便對別人說,但因為他相信中脩三,覺得跟他說也無妨,才會在日記裡寫下這些心情。
前面提到,在前一日吐露愛情困擾的日記裡,甚至在更早以前,「內臺差異」就已兩人對話中的一個潛藏主題。A君似乎一直清楚意識自己的台灣人身份,而是從「我們台灣人」的立場,與中脩三討論自己的困擾。然而,中脩三不知是無法察覺或故意忽略,並未正視這個問題,使得A君不得不有話直說。A君直白的質問,顯然讓中脩三自覺權威受到威脅挑戰。他對A君日記作出非常長的批示,幾乎與A君日記原文一樣長,這其實有些背反森田療法講究從經驗體悟而非道德說理的原則。事實上,中脩三似乎被觸怒了,或是有些倉皇失措,他的回覆不像先前那麼充滿哲理,而是更為直白,而且有些凌亂。
然而,中脩三還是沒有正面回應「內臺差異」的問題。他責備A君身在台灣又才二十五歲,應該保有青春意氣,絕不應為了感情困擾放棄學業。他說A君若只想依靠父親財產,不想努力求學而只想成為一個像他父親一樣的平凡百姓,那他就應該與他的養妹結婚。反之,若他想與心愛的人結婚,那他就應該努力開拓自己的世界。他警告A君若他在還未能獨立前結婚,那就等於放棄自己的人生。中脩三稱讚A君頭腦清楚,將來一定很有成就,但不應再沉溺文學,不應再為感情而盲目軟弱。他提醒A君世上唯一可信只有真正的學問,憑藉真理可以支配任何人,他要A君無論哲學、經濟學或醫學都好,應該立志作一個學問、真理的探究者。
至於就A君所提的本島人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中脩三的回覆並未觸及其結構性因素,反而是質疑A君現在就在考慮畢業後的就職與社會地位等問題,「是不是太過現實主義?」他說一個人若是身負才能,一定會得到別人肯定,而且就算未得他人肯定,也一定能開拓自己的道路。他要A君要具有世界觀,「看看想獨立的菲律賓」,「張大眼睛看看南中國廣闊的田野」,「看看印度」,「看看澳洲」,「想想我們可以飛躍的天地有多麼的廣大!」他鼓勵A君應當立志與西洋對抗,把東洋建設為東洋人的東洋,還說若A君埋沒自己的才能,將會是東洋民族一個很大的損失。
「筋肉是萬有的基礎!」
然而,此時中脩三所說的,無論是學問真理的理想,或是東洋民族的願景,都已無法打動心意已決的A君。在出院前一天(五月二十日)以及出院當天的日記裡,A君提到他曾經認為自己最適合成為一位學者,他也贊同中脩三所言「我們東洋的現狀正在呼喚有為青年」。事實上,他並不是對東洋情勢無感,也體認東洋民族需要熱情與實力,若不是想要對東洋有所貢獻,他也不會在工業學校畢業後又絞盡腦汁考入高等學校。他很自豪自己或許頭腦不好,但卻有著絕不屈服的「戰鬥精神」。然而,在生病以後,不知是幸或不幸,他對很多事有了新的體認。他現在認為只是為了學問而學問、走不出象牙塔的知識,並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可笑。而且他覺得以他目前的身心與家庭狀態,若是回到學校,病情一定會再次加重。因此他已下定決心,他要回到家鄉繼承父親土木包商的工作。他體認到在現在這個世界中力量就是正義,男人就是要有力量,他想要以其在工業學校土木科所學,做好土木包商的工作,累積更多代表力量的財富。他還說現在「台灣地方自治制」已經實施了,他想要以故鄉為地盤,為自己搭建將來活躍的舞台。他強調這絕不是「拜金主義」,而是他現在體認到曾經唾棄的金錢的效用,他會為了「鄉國」、為了「東洋」好好善用財富。
此外,A君也為自己的感情困擾做個總結。他說他當然知道戀愛會使人盲目,也不曾有過要為愛情放棄一切的念頭。但是即使他將前途放在首位,他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感情,因為他是自從有了愛情之後,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才有了為國家、為東洋貢獻的元氣。他自嘲或許是天生性格的緣故吧,對他而言,沒有家庭就沒有國家,沒有東洋,他的愛情是「以前途為前提的愛情」,前途與愛情二者他都不能放棄。
至此,A君說他應該跟中脩三說的話都已經說完了,他以後再也不會提起相關問題。他相信中脩三所說若是他能更精進自己,自然就會明白真正的道理,他也會把磨練心力當作今後的課題。最後,A君寫到「無論如何都要先鍛鍊身體。先讓自己變笨,好好做好蓋房子的工作吧!」
對於A君的總結,中脩三的評語是「這樣很好!找到出路了。將來的事將來解決。先鍛鍊筋肉吧,筋肉是萬有的基礎!」
於是,這一例也許是台灣最早留有記錄的心理治療,有著非常「肉體性」的結語。
後記
無論如何,A君自養神院出院後,應該仍與中脩三保持著聯繫。中脩三在1945年發表的心理治療摘錄末尾,提及A君的近況。A君最後似乎還是完成了台北高等學校的學業,十年後的他,已是從京都帝大畢業正嶄露頭角的法學士,此時在某南方會社努力工作,為「大東亞」、為「十億民族」奉獻心力。中脩三強調「有為的人才也比較容易受環境影響,為了確保不浪費人才資源,絕對有必要進行如《心理と医学》這本期刊所刊載的這類研究。」他總結說「大東亞的建設,要旨在於民族相互真正的理解。醫師的使命就在於個人的、直接的增進此理解。」
然而,中脩三真的了解A君嗎?A君又是否覺得中脩三真的了解自己呢?不知中脩三與A君各自如何闡述兩人於治療中的交會,如何解釋這段治療對彼此的影響,但是閱讀這篇記錄後,不由自主覺得A君最後「該說的話都已說完」、「以後不會再說了」的感受,似乎是這段心理治療很好的註解。在心理治療中,當被治療者覺得已無話可說,治療者也不想再說時,治療就已圓滿了吧。多說無益,面對現實,殖民體制中異民族的相處應該也是如此。森田正馬希望他的療法幫助神經質性格者鍛鍊最好的適應性,能夠融入任何情境,在客觀現實中實現自我。諷刺的是,中脩三對A君的治療在某個意義上或許真達到了這個目標。畢竟,若是連面對兼具殖民統治階級與治療者雙重優勢身份、高談闊論「大東亞」的中脩三,A君都能泰然自若,那他應該能適應任何現實環境而遊刃有餘。無論如何,從結果看來,心理治療對A君也許真有幫助也說不定。心理治療就是這麼奇妙,它是一種有效的療法,但沒有人確實知道它為何有效。
參考文獻
中脩三,〈本島人青年の煩悶とその指導〉,《心理と医学》,第一卷第三號,收錄於岡田靖雄編,《精神障害者問題資料集成・戰前編》,第12卷,頁148–152(東京:六花出版,2016)。
森田正馬,《神經質の本態及療法》,收錄於《森田正馬全集》,第二卷,頁279–442(東京:白揚社,1974)。
森田正馬,《戀愛の心理》,收錄於《森田正馬全集》,第七卷,頁23–183(東京:白揚社,1974)。
廚川白村,《近代の恋愛観》(東京:改造社,1922)。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 戀愛至上或非關愛情?一份本島青年的心理治療記錄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