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
這陣子有兩個不太多人留意但卻有點重要的新聞。其一是,金管會日前宣布 ,我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簽署了一項合作協定,參加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俗稱「肥咖條款」)延伸出來的國際計畫。「肥咖條款」是為了要求外國(即台灣)的金融機構協助確認美國籍大戶,必要時得懲處不配合的金融機構。在宣布後,金管會表示將依2015年通過並生效的《條約締結法》完成後續程序。
另一則新聞則是立法院的內政、財政委員會剛完成《台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初審,將過往由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澳門航空公司簽署的「互免航空公司稅捐瞭解備忘錄」提升為官方版的協議 。
據評估,該協議可帶來稅收淨增加1.58億元,也讓陸委會有落實監督的法源基礎。也因為這個新聞,才讓大家注意到原來有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這類法規影響著台灣對外關係的議定,程序寬嚴對各事業發展也有很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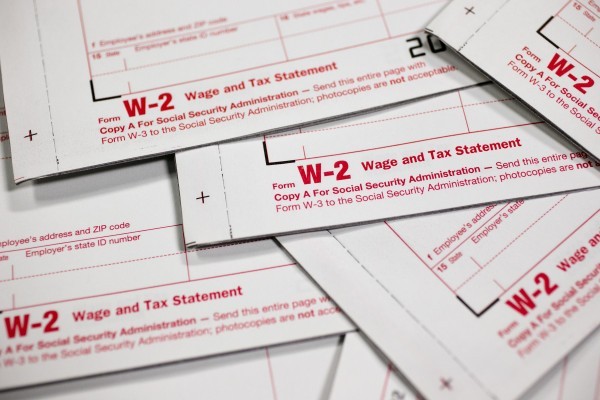 「肥咖條款」是為了要求外國(即台灣)的金融機構協助確認美國籍大戶,必要時得懲處不配合的金融機構。(資料照,彭博社)
「肥咖條款」是為了要求外國(即台灣)的金融機構協助確認美國籍大戶,必要時得懲處不配合的金融機構。(資料照,彭博社)
不過,國際條約是什麼呢?
說「條約」是規範國際關係的法源有些抽象,不如說「條約」是最容易舉證且適用的白紙黑字:答應就是答應、拒絕就是拒絕,一拍兩瞪眼。但其涉及的法律爭議如星斗般繁多,比如條約產生的法律效果、約文解釋上的矛盾、針對特定條款的保留,甚至與其他國際法法源(諸如習慣、法律一般原則)之間的關係。
一般來說,條約整個締結程序 包括:談判約文➙簽署確定文字內容➙帶回國內讓國會批准➙簽署後寄回約定機構存放;而本文想著重在那個「國際法」與「國內法」交錯的環結上:條約締結的國內程序。
國際法下的條約
1969年通過、1980年生效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是國際法中關於條約規定最主要的法律基礎:也就是由條約來規範如何定義並解讀條約,而「條約」是指國家間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的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如公約、協定、諒解備忘錄、過渡辦法)或兩件以上相互有關的文書(如外交換文、商定記錄),名稱五花八門。 諸如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都算是一國在國際上確定接受條約拘束的「法律行為」。
不過須注意的是,有時候「簽署」就等於同意承受條約的拘束,而這得視條約本身的相關規定,通常會在談判時就先講好。總之,條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協議必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也就是凡事不打臉,才能維持良好的國家誠信與穩定外交。
自19世紀以來,條約的國內程序才開始流行,即一旦完成批准,就等於同意被條約拘束。批准後,就算條約本身還沒生效,該條約也對批准國產生拘束力。也就是說,不管國內社會紛紛擾擾,批准國都「不得妨礙條約目的及宗旨的義務」。 在等待正式生效的期間,遵照「不打臉原則」,除非條約人氣太低一直達不到要求的批准數量而生效不了,那大家最後就摸摸鼻子算了,不過多久是「太久」視情況而定。
近代條約都附有「最後條款」(final provisions)的部分,會說明簽署後,代表拿回國內應該做什麼,而無論談判、簽署、批准、遵守(或耍賴)都要有國內的民主正當性並符合國際法。事實上,19世紀中葉以來,「批准」逐漸從形式走向實質審查,也象徵締約權力由行政權移轉至立法權,最後成為當代國際法的重大變革之一。漸漸地,「國內批准程序」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不過國內如何批准則由各國自行決定,這點國際法管不著。這個趨勢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越來越多「造法」(law-making)條約的出現-即不只是國家間的和解、互助或其他瑣碎的約定,更包含追求規範化、普遍化的意圖。因此,更講求程序正當性。當然也與當時強國們法制發展相呼應,比如私法上書面契約的優勢、公法上國會保留的崛起,以及習慣法法典化的興盛等。同時,國際間的非正式文書開始退流行。
 1969年通過、1980年生效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是國際法中關於條約規定最主要的法律基礎。(Reparation Law)
1969年通過、1980年生效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是國際法中關於條約規定最主要的法律基礎。(Reparation Law)
條約批准的法律與政治意涵
從社會契約的角度來看:一份A國與B國的協定=(A國人民的契約授權A政府)+(B國人民的契約授權B政府)作最好的安排。因此,對A、B國各自的人民而言,條約批准可以視為對該項安排進行最後的確認與同意,而這個行為也將一份國際協定,從一紙沒有法律效力的文書,轉化為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
條約生效前的每個步驟中,除了談判與存放外,「簽署」和「批准」更涉及了國內社會的反應,比如代表授權、國會審查等,這也與憲政秩序中的權力分立大有關係。作為臨時踩煞、力挽狂瀾的最後閘口,「批准程序」的設置及設計很重要。
誠然,交給國會檢視條約內容,能藉此制衡行政權;然而,若立法權太過膨脹,卻可能造成行政效率低落或政策推行不效,有時也會錯失締約的良機。不過,並非所有國家都是以國會作為最後的決定機關,比如中國的《締結條約程式法》第7條規定,條約批准「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雖然人大的常委會已是中國憲法上的釋憲暨立法機關,但關於條約批准的決定,最後仍須由中國國家主席再「予以批准」才算數。
或像是總統制的美國,由於政府與國會屬於對抗關係,因此對於條約批准程序還蠻嚴格的,一般來說不僅談判代表須先經國會選擇並授權,需要定期會報,簽署後也要2/3的參議員同意才行。不過,具有時效性的貿易協定另當別論,1974年通過的《貿易法》例外提供了「快速審議程序」(fast-track procedure),但這裡就不深入說明了。
又如內閣制的澳洲,因為行政權與立法權一致,憲法原本就授予政府極高「關於對外事務的權力」,且嚴格來說憲法原本並沒有要求國會許可。因為君主立憲的關係,批准程序中還多了一道「御准」(royal assent),現在實際操作上已不由英國女王操刀,而由澳洲聯邦總督完成這項形式上的要求。
由這些例子可見,國內批准程序的設計和各國本身的政治體制與發展息息相關。
基本上,一份條約批准後,同時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效力。前者是指一國因條約,而與他國產生權利義務的變動;後者則是為了履行條約,可能需要調整國內法規。因此,「批准」不只是人民授權國家以承擔國際義務,也具有政府與人民之間雙向溝通的功能。
台灣的條約批准程序
在2015年通過《條約締結法》之前,我國大都以1993年的大法官釋字第329號解釋為主。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大法官有特別提到:兩岸協議,不是「國際」書面協定,因此不在解釋範圍內。可見我國對條約的國會審議程序,基調是採「中國以外國家」與「中國」雙軌制。
事實上,這個憲政秩序依然被維護著,對於與非中國之外國締結條約才會依《制定條約締結法》(2015年7月1日通過,取代同月27日廢除的《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其中,需要「被批准」的條約內容包括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涉及國防、外交、財政或經濟上利益等國家重要事項的,或涉及與國內法律內容不一致而須修、立法等情況。
關於條約的談判與批准,原則上由外交部(或協同其他業務機關)進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外交部沒有義務向立法院說明談判內容或進度。不過,要簽約時,需要行政院的授權,而簽署後須送立法院審查。立法院的審議結果可能包括:
(1)提出條約保留的條款;(2)如果覺得特定約文不妥,可以退回重新談判;(3)但也有可能整份GG;(4)要是審議通過,則由總統頒發批准書,並完成其他國際與國內程序,就大功告成啦!
另外有一種情況是,文件本身不是條約或沒有「最後條款」時,雖然也會以「條約案」處理,但這種特殊情況通常是因為協議內容將不影響原來的國內法律秩序,因此要嘛本來就有法律授權,要嘛事先已經立法院同意,所以主辦機關只須送行政院備查,生效後直接由總統公布,並送立法院查照即可。但也發生過像《臺美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的窘境,送到立法院時,被要求改為實質審查,表示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出現認定不一致又溝通不良的問題。
 在2015年通過《條約締結法》之前,我國大都以1993年的大法官釋字第329號解釋為主。其中特別提到:兩岸協議,不是「國際」書面協定,因此不在解釋範圍內。可見我國對條約的國會審議程序,基調是採「中國以外國家」與「中國」雙軌制。(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在2015年通過《條約締結法》之前,我國大都以1993年的大法官釋字第329號解釋為主。其中特別提到:兩岸協議,不是「國際」書面協定,因此不在解釋範圍內。可見我國對條約的國會審議程序,基調是採「中國以外國家」與「中國」雙軌制。(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除此之外,台灣與非中國之外國間的經貿類協定,依《貿易法 》(1993年公布,最近一次於2013年12月修正)第7條辦理,也是較《制定條約締結法》簡易。至於涉及中國(大陸地區)之whatever協議(通常不用條約或協定等正式國際文書的名稱),皆依1992年制訂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由陸委會專責籌辦。除非涉及修、立法,須送立法院議決外,原則上簽署後,由行政院核定、立法院備查就好了。
結論
最後要來談談,批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條約一旦批准,即產生國際法上的效力了,代表全民都得參與這一份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國際遊戲規則。我國《憲法》第141條就規定了:
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
不論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有多麼特殊,基於尊重國際法治的精神,我國實務見解大都給予國際條約「特別法」的地位,因此優於普通法(即國內既有的法律規定),因此,不論台灣要締結或審議任何條約(或協定,或協議),大家都應該多多給予關注與討論,尤其是可能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部分。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看看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074號判例(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內中國法院之協定)、最高法院72年臺上字第1412號民事判決(關於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法務部72年法律字第1813號致外交部函(關於中賴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臺灣高等法院79年度上更(一)字第128號判決(關於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及最高行政法院93年判字第281號判決(關於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WTO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參考資料
Hathaway, Oona (2008). ‘Treaties’ E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17 *The Yale Law Journal*, 1236-1372 Hudson, Andrew (2014). ‘From negotiation to implementation: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Asia Pac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Network on Trade**** Policy Brief**, No. 44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66),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with commentaries , 1966,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 II
Lantis, Jeffery. The Life and Death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Double-Edged Diplomacy and The Politics of 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李建良,《論國際條約的國內法效力與法位階定序》,收錄於<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八輯)>,2014年,頁175-278 許耀明,
《未內國法化之國際條約與協定在我國法院之地位》,<司法新聲>第104期,2012年,頁20-27 廖福特,《批准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及制訂施行法之評論》,<月旦法學雜誌>第174期,2009年,頁223-229
法律白話文運動/【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專題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