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訊》總編封德屏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叢昌瑾攝)
《文訊》總編封德屏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叢昌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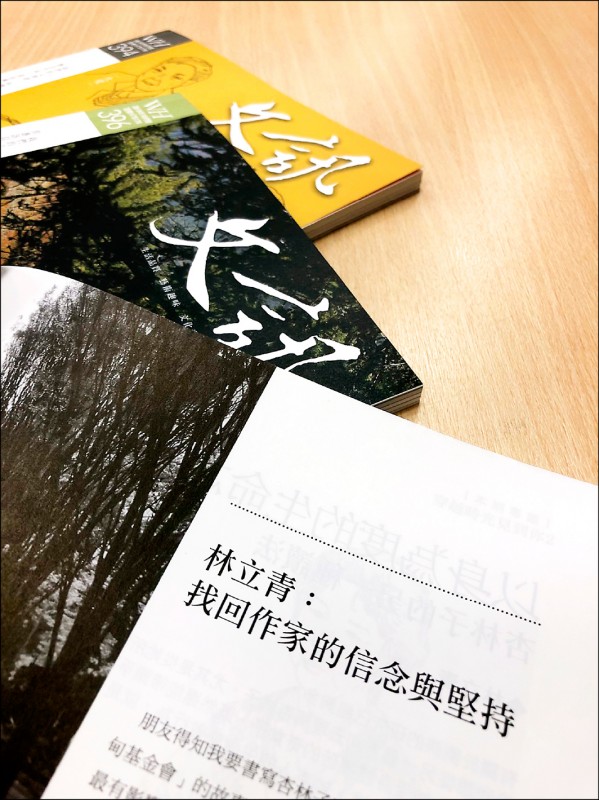 《文訊》堪稱台灣文壇生命線,只要有文學新書刊物,本本都會收錄典藏。
《文訊》堪稱台灣文壇生命線,只要有文學新書刊物,本本都會收錄典藏。
在許多文化人心裡,《文訊》不只是一本有36年歷史的文學月刊,它更像是文學作者與愛好者的家,這個家2017年初從張榮發基金會大樓的6樓,搬到日夜都見不得光的B2,大廈的樓層板上清楚標示各公司行號,只有B2是一片空白,隨著電梯沉入地底,觸手可及的天花板讓人很有壓力。
《文訊》擁有台灣最豐富的文學資料庫,因為《文訊》,這棟大樓,成為國內外華文學研究者必定要造訪的資料重鎮,總編封德屏指著資料庫裡的書架,介紹每個作家的資料與墨寶笑逐顏開,轉頭回到辦公室看到擱在桌上的攏共16萬的房租繳費單,不禁眉頭深鎖,因為一天都不能遲交,花16萬租下200多坪的辦公廳舍,很多商家認為划算,但對《文訊》來說,16萬卻是每個月都快喘不過氣來的重擔,「大家有時都愛說我是俠女,但我寧願自己是能劫富濟貧的廖添丁」。
回想2003年,國民黨文傳會決定結束既不賺錢、又沒能帶來選票的《文訊》月刊,讓文學界不分藍綠、放下統獨立場投入搶救,文學大家們有的捐墨寶,有的則以自身影響力呼籲各界捐款的,就是想留住這一個文學園地,「當初《文訊》被無預警結束的前後,有兩間學校想找我執教鞭,可以有安穩的生活與收入,但想了一晚,最後我還是留在這裡,為《文訊》也為文壇做一點點事。」在幾場義賣會下,《文訊》終於籌得兩千萬,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但就如尋常人家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要錢,一本純文學雜誌要在台灣永遠不景氣的文化界裡活下來,更是件不容易的事,封德屏不能只在書海裡舞文弄墨,每天進辦公室盯的是密密麻麻的會計報表,「月刊獨立好幾年後,才知道原來我是要運籌帷幄的人。」
別的CEO努力賺錢,封德屏運籌帷幄的卻是如何守住純文學那道微弱的螢光,文學江湖後輩總愛叫封德屏「封姊」,這聲「姊」不只是敬重,那是因為她更像媽媽、姊姊一樣照拂文壇眾生,張曼娟初出文壇時,《文訊》曾經不遺餘力支持她創作;老作家生計困難時,封德屏也帶著眾兵將,為作家申請社會急難救助,甚至有些孤苦無依的老兵作家,身後事也都是《文訊》一手打點;作家日思夜想的是作品能有發表園地,《文訊》則為資深作家創立「銀光副刊」,作家過世後,不論是否有名無名,或大牌小牌,《文訊》也一定推出紀念專刊,至於每年九九重陽更席開40桌,從《文訊》都會交次安排資深、新進作家們團圓一桌、交流心得,就能看到她的細心。
在紙本式微的當代,只要有文學新書刊物,《文訊》必定本本都收錄,「這是文化薪傳。」封德屏說:「我知道這樣很像螞蟻在搬書,但是只要這些書冊還在,即使斯人已遠,他們的靈魂與生命都還會透過這些文字延續下去。」作家端木方生前曾用寫實筆法寫出1940年代華北地區的風俗,過世後,《文訊》為其出版專刊並計畫舉辦特展聯絡家屬,並詢問家屬手中是否還能提供某些已經消失在市面的孤本,「端木方的太太接到電話後,才知道原來這麼多年後,還是有人記得他的作品,頓時泣不成聲。」去年正式對外開放的資料中心裡面就收羅了許多早已絕版的書稿文刊,大河小說《浪淘沙》的作家東方白參觀過資料庫後,就驚嘆除了自家書房,在全世界,大概只能在《文訊》資料庫裡可以看到最齊全的東方白著作。《文訊》儼然已是台灣文壇的重要生命線。
《文訊》的另一條生命線,則是位在台北城南的紀州庵,這座日本時期是高級日式料亭的市定古蹟,成為1949年後新住民的家,王文興一家人定居於此,成為經典小說《家變》的場景,八年前台北市政府又委託文訊經營,衰頹的古蹟搖身一變成為台北最豐美的文學森林,幾乎每天都有大小藝文活動,走在同安街上,路面不是黑漆漆的柏油,馬路成為鑲嵌著詩句的詩風景,「當初,很多朋友都勸我別做,因為我是館舍經營的門外漢,朋友都認為不會有好結局。」但是任性的封德屏不顧反對接手館舍,她的韌性讓紀州庵至今已經辦過兩千多場演講,量多質精,甚至在這裡還能吃到作家的私房菜,「紀州庵讓我將文學理想實踐在立體的空間裡,我們也走出了同溫層,接觸到更多愛好文學的群眾。」
紀州庵獲得鄰里的認同。瑩圃里里長陳木松一知道紀州庵文學森林爭取同安街人車分道多年未果,立刻向北市府反映,現在走在同安街往紀州庵的路上,不再需要與車爭道;河堤里里長鄒士根將里民活動中心定位成文學森林的前哨,除了張貼「前方兩百公尺就到紀州庵」的標誌外,更在活動中心裡擺放多份文學活動刊物,看到這些回饋,封德屏好生感動:「每當走在同安街上,人們喊我館長時,我都好感恩,感恩老天當初給我們這片文學森林的機會。」
在許多資深作家眼裡,封德屏只是小妹,但她日忙夜忙已從青絲忙到了華髮,不時還會被問及一旦她老了退休了,《文訊》該怎麼辦?封德屏先笑稱自己早就老了:「我是個不太懂管理的人,唯一知道的只有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封德屏對文壇不求回報的俠女精神,早已浸潤《文訊》的每個角落,但她仍有掛心事,「百分之八十的作家都活動在台北,但國家文學館在台南,台北也很需要台灣文學記憶的展示空間,台北目前沒有這個空間,但《文訊》有,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與更多人分享。」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