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
一直以來,台灣的法律採借西方的法律條文或理念,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同時還是個必然。令人驚訝的是,台灣的法律學界對於所採借的西方法律和理念如何與「常民的法律和理念」碰撞,以及碰撞之後發生甚麼事的研究,卻又少之又少。這個情形在死刑存廢與否的論爭裡也不例外。
 一直以來,台灣的法律採借西方的法律條文或理念。(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一直以來,台灣的法律採借西方的法律條文或理念。(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一位法律學者直接告訴我,法律的制定要取法於最為保障民主、人權的條文和精神,只要在立法這個層面努力讓法律通過,人民如何感受也不是那麼關鍵了,畢竟「頭過身就過」,人民總是需要再教育的。死刑存廢的辯論也是存在西方法律理念與「常民的法律和理念」碰撞之後的矛盾,只是死刑存廢關係著文化裡面最深最廣對生命、人的價值的假設,這種矛盾便顯得張力十足,因為每個人都可能牽涉在其中,不像其他西方法律的引進所帶來的矛盾,可能是只有局部的。
這個張力,借用陳嘉銘教授在2010年「死刑存廢:道德、政治與法律哲學的觀點」座談會中的用語:「廢死運動的人權論述和台灣社會的存死話語,好像二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一個來自歐洲『文明』星球,一個來自台灣社會星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4: 236)。蕭高彥教授在同一場座談會中也說,「在台灣社會中,廢死論者具有高度的人道精神,並且基於國際組織相關的協議書,以及英美關於死刑是否合憲的學術討論和司法實務,已經產生相當完善的論述以及社會運動策略。相對的,反廢死論者往往以主要的受害者家屬為代言者,通過感性的說法來表達他們的訴求」(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4: 243,強調為我所加)。
真實的狀況當然遠為複雜,不過這「二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似乎架構了死刑存廢與否論爭的主要面貌。同時無論正反雙方,都有來自法律、政治、哲學、宗教的專家,提供系統的論述,人類學有甚麼不同的話語可以參與這場公共議題的辯論呢?
讓我們先看一場關於死刑的公眾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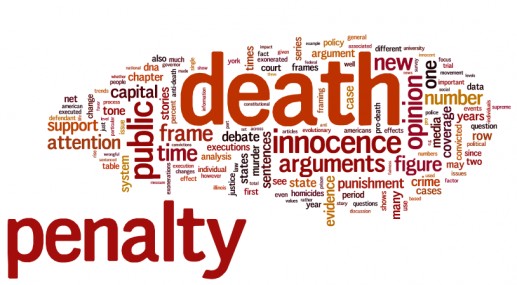 「二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似乎架構了死刑存廢與否論爭的主要面貌。
「二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似乎架構了死刑存廢與否論爭的主要面貌。
砲聲隆隆的死刑存廢論壇
幾年前我受邀參加南投縣某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討論死刑存廢的公共論壇。那是一個跨課程的活動,論壇的地點選在國小的禮堂,我到的時候,國小禮堂裡擺放的二百多張鐵椅幾乎已經快坐滿了。主辦單位找了三個與談人參加論壇,我到了之後才知道由於是「廢死聯盟」推薦來與談,我已經被設定好是廢除死刑意見的代表,一位社大學員擔任贊成死刑意見的代表,第三位是位退休的法官,偶而在社區大學開設法律常識之類的課程,他則扮演解釋法律規定的中立角色。
法官首先引言,提出一些死刑存廢的背景資料,我則趁此同時看看底下的學員聽眾,那是和我在大學教書所習慣的學生族群完全不同的組成,有各種年齡(當然以中高齡居多),看起來各種行業都有(有公務員樣貌的、做小生意模樣的、更多的是「婆婆媽媽」)。接著換我提供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我並沒有依照「廢死聯盟」準備的說帖來發言,也許是剛才觀察底下聽眾之後的感覺吧。最後是贊成死刑意見代表的發言,我發現她沒有任何的「說帖」(正式的理由),她只很簡短的描述她的感覺,作為一個「老百姓的想法」(她的用語)。接下來是開放問題,讓學員聽眾和與談人交換意見。整個Q&A部分下來,一共有五位學員聽眾發表意見加提問,而且清一色都是問我問題,或是說針對主張廢除死刑提出疑問。由於當場採取即問即答,整場的氣氛倒像是個質詢。國小的禮堂迴盪著的聲音,光就提問的問題以及它們得到不少掌聲的鼓勵,讓我感覺到:法務部所做的民意調查中,台灣有近8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是如此的迫近。
我感覺我像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在一個不該出現的場合說出一些不受歡迎的意見。在幾個不是很友善的問題之後,氣氛逐漸緊繃,一位就坐在我對面前排看起來極為年輕男性,緩緩的說,「若是取消死刑,那麼有錢人最高興,因為他們可以花錢找人把他們不喜歡的人殺掉,也不會有事,那如果被殺掉的人是你(也就是我)的親人,你要怎麼辦?而且為什麼我們要出錢養壞人?」在那一刻,我覺得主張廢除死刑的人被等同加害者,或是要為加害者的行為負起責任,至少是要連帶承擔一般「老百姓」對暴力加害行為的憤怒與不平。同時,我也覺得「大學教授」的頭銜似乎是讓我能夠繼續發表不受歡迎意見而不被立即趕出去的最後護身符,因為幾位提問者在激動的陳訴自己的意見之後,會加上「這是我小小的意見,敬請教授指教」。
但是,我正好是「(法律)人類學者」,讓當天的結果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最早的二位聽眾的發言,很明顯的是非常普遍的反對廢除死刑意見:(一)、廢除死刑會讓社會治安變得更差,因為作姦犯科者沒有死刑的嚇阻,就會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二)、死刑犯不大可能悔改,廢除死刑只會把死刑犯放出來,讓殺人犯會滿街跑。(三)、一命抵一命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廢除死刑那麼被害人家屬的權益無法保障,被害人的冤屈也無法平反。或是用另外一種類似說法,受害者家屬的傷害要如何彌補?
我根據「廢死聯盟」準備的說帖與數據來回答這些疑惑,例如,(一)、現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沒有死刑,沒有任何研究顯示無死刑的國家的犯罪率比維持死刑的國家還高。犯罪率的因素很複雜,包括教育、社會公平正義等,提高破案率更能維護治安。(二)、台灣暫停執行死刑四年多來,殺人犯並沒有滿街跑,世界上139個廢除死刑的國家,殺人犯也並沒有滿街跑,廢除死刑不代表廢除所有刑罰,犯罪者仍須為其所行為負責、接受處罰及隔離於社會之外。(三)、死刑是不是真的可以撫平受害者的傷痛?有許多民間社團朋友們以及政府社會福利機制,正努力地推動著各種刑案受害者與受害家屬的社會補償、支援救助以及身心輔導等措施。反對死刑,也可避免在體制的失誤下,有更多受害者產生。
緊接著的一位聽眾的發言,針對我的回答,直接了當地說,我提出的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都是取自國外的經驗,國情不合啦,西方國家是文明的,所以可以採取這些措施,但是我們台灣還沒有到達這個水準,不能去學別人的作法,作了壞事就有所報應,天理才會有所循環。也就是說大多數民意贊成死刑,廢死論述只是菁英決定的啦。他說大多數民意贊成死刑,在這個體育館內是很容易證成的。我頓時感到有點尷尬,就如同台灣官員和法律界人士在來訪的外國法律教授面前,難以解釋所謂的「國情不合」,難以解釋「台灣還沒有到達這個水準」;只是我的尷尬和前者正好是相反的方向,前者是法律界人士難以向外國教授解釋「台灣還沒有到達這個水準」,而我的情形則是「老百姓的想法」清楚地向我解釋,「台灣還沒有到達這個水準」,此時我被當成外國教授。
我被當成外國教授在這樣的公共論壇裡,其實是極富意義的。我不僅在陳述一個不受歡迎的意見,我同時在陳述一個「外國人」的意見,一個「國情不合」的意見。我驚覺我的尷尬(這是某種人類學講的文化震撼嗎?)根源於我和在場的多數民眾講的是不同的「語言」。我於是改變策略,我曾經作過許久的鄉鎮調解委員會的研究,聽到的都是「老百姓的想法」,因為那裡沒有硬梆梆的法律文字,我怎麼會忘記呢?
於是我說,一個典型的車禍案件調解總是如此開始的:傷亡者或親屬敘述著自己的痛苦,不論是身體的痛苦或是看到以及照顧傷者的痛苦與辛苦,然而這些痛苦都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是因為對方開車時候的錯誤或過失的話。接著,說話者的火氣可能越來越大,說話的聲音越來越急促與大聲,特別是說到對方自從車禍事件之後,既沒有到場看望傷亡者,甚至連一通關心的電話也沒有,好像是車禍對傷亡者造成第一度傷害,之後對方的不聞不問更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對方對於此項的「指控」,也總是給了許多的解釋(當然默認傷亡者及其親屬說法的也很多),包括要去看傷者時正好不在,電話沒打通等等。最奇怪的是,常常看到當一方說他曾經去看望過或是打過電話給傷亡者或其親屬,而傷亡者這方也不否認這個說法,但是傷亡者這方還是進一步用其他的方式說對方沒有給予應有的看望及關心。
我主要的論點是,當代法律是從權利(rights)開始,傳統法律是從錯誤(wrongs)開始的。從關於錯誤開始的傳統法律的核心概念是損害或傷害,任何一個傷害都需要被彌補,否則原來的社會道德、秩序無法恢復原狀,如果一個人做出違反習俗或是規範的行動,到了最極端殺害人命,那他負的債就大到只能用生命去抵償了。然而現代的法律從天賦人權開始,人的基本權利是從出生就具有,甚至是早於國家的,國家是人民合意來保護人的基本權利,而不是去剝奪它,所以死刑的存在是和當代的國家、法律建立的基礎相違背的,同時被害人家屬的補償必須以其他的方法來達成,不再是一命抵一命。
 當代法律是從權利(rights)開始,傳統法律是從錯誤(wrongs)開始的。(擷至網路)
當代法律是從權利(rights)開始,傳統法律是從錯誤(wrongs)開始的。(擷至網路)
我不知道此番根據我法律人類學研究成果的綜合論述,達到多少效果。不過,最後一位聽眾對我的提問,除了繼續表達他對廢除死刑的憂慮之外,卻多了想要了解傳統法律文化的興趣,他說,「傳統和現代都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什麼時候傳統比較多?什麼時候現代比較多?要有什麼契機可以讓傳統和現代做個調合?」同時,最後的總結時,另外二位與談人也緩和地指出,我們目前是處於歷史進化的時刻,法律文化不斷的在轉變,今天的公共論壇的討論可以讓大家思考看看傳統法律文化是什麼,有沒有需要改變的,二十、三十年之後,不管那個時候台灣是否廢除死刑,我們的討論對於後來的人作決定都會有所貢獻。「公共論壇」準時在晚上九時結束,二百多個人從私人家戶走出來參加在公共空間舉行的一個和公眾有切身關係的死刑存廢的議題,然後大家再回到私人家戶,對於這個公共議題是否有和進到這個公共空間之前有不同的體認?
我自己作為那個特定公共論壇的參與者,從原來的類似法律人廢除死刑的主張,在當場所感受到的尷尬或震撼,看到死刑存廢的辯論似乎走到一個死巷(cul-de-sac),因為它的命題範圍變成我們是否要贊成西方「先進」理念是否以及如何讓一般老百姓了解與接受。我慶幸我法律人類學的研究讓我敏感到這個議題方向的沒有建設性,我嘗試以我認為的「老百姓的想法」點出它的歷史性,把此議題至少部分導向成我們是否要贊成「傳統」法律理念可以不需要被檢視。換句話說,我嘗試將當場的討論從直接的「國情不合」,變成我們對自我的搜尋(soul-searching)。我成功了嗎?我提出了一個對於這個公共議題可能的問法,而我是從法律人類學的研究開始(當然,這個可能的問法最後也要變成公共辯論裡被批判檢視的一環)。
 來源:http://talk.news.pts.org.tw/2010/05/4.html
來源:http://talk.news.pts.org.tw/2010/05/4.html
法律人類學可能的介入
人類學有甚麼不同的話語可以參與關於死刑的辯論呢?在這涉及文化中對於生命與正義的公共討論中,人類學有沒有可能清楚陳述出當代台灣人文化信仰體系對生命價值的態度?如果我們認為「廢除死刑」與否、以及它是否成功,只是法律、政治問題,主要依靠著法律理論的辯論或是國際、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那麼文化信仰體系便永遠只像是個難解的激情,甚至是容易被操弄的對象。人類學常常賦予自己探索「難解之謎」的使命,但是也許最後說起來它們之所以難解,其實是因為它們在理性的觀照下顯得沒有系統和規律,更何況了解它們畢竟不只是著眼於法律的修改而已。
所以要了解文化信仰體系得包括文化人類學在內的在地和比較研究,也正是在此我認為法律人類學對「廢除死刑」論爭可以提出二個新問題,投入這場公共辯論裡,試圖連接「二個星球」。一個是貼近並掌握文化的信仰體系,另一個是找尋轉化的機制,消解死亡所造成 的「債」。而且這二項動作是習習相關的,因為貼近並掌握文化的信仰體系並不代表是無條件接受它們,而是加以了解並且找尋轉化的機制。
法律人類學主張要去面對台灣法律長期移植、混合西方法律的社會實況,強調對法律現象的解釋需在掌握社會文化的脈絡上進行,對死刑的論爭也無例外。透過當地人「正義觀」的表現方式,進而整理出當地人的文化形式、文化關係是值得探討的。地方「正義」觀,一方面深受現代法律和政治系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卻又是當地人據以落實和轉化法律正義的一組觀念,甚至帶有挑戰法律正義的能動性。人類學與法律可以從彼此的合作中互相受益。如此一來,關於死刑存廢的辯論能有更具體的設定,法律專業人士可以多一點了解常民的想法,人類學家可以傳遞地方的法律知識來形塑死刑存廢的討論內容。在這個廣大的公共空間的辯論裡,(法律)人類學家既是中介者,更是提出問題者,一如我在社區大學的論壇可以做的事,只是這些可能必須建立在清楚的經驗研究上。
 關於死刑存廢的辯論能有更具體的設定,法律專業人士可以多一點了解常民的想法,人類學家可以傳遞地方的法律知識來形塑死刑存廢的討論內容。(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關於死刑存廢的辯論能有更具體的設定,法律專業人士可以多一點了解常民的想法,人類學家可以傳遞地方的法律知識來形塑死刑存廢的討論內容。(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鄉鎮調解會的研究中,我理解到台灣社會人與人的互動,還是充滿著社會義務網絡的道德表述,在常見的民事糾紛就已經非常濃烈的表述出來償還的義務,那麼在面對最為重大的損害——死亡——時,償還的義務的表述一定會更加濃烈。因此我覺得廢除死刑的論述不能只著重在先進法律保障權利的爭議點上,廢死論述還必須要提供轉化的機制,讓人們在死亡事件上一方面可以表述出死亡所帶來的對生活世界重大損失的缺憾,另一方面在建構新生活世界意義的同時,讓當事人感到償還的義務已經解消。
人類學家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在’Anthropology as a Moral Science of Possibilities’一文中,期許人類學可以成為挖掘出道德可能性(moral possibilities)的科學,希望人類學可以找到道德的美學(moral aesthetic),打開我們觀看、理解世界的可能性,這個途徑就在於人類學能不能解開像是法律語言只是限縮人們世界的道德語言,把各文化裡各種論述形式找出來以掌握說話者豐富多樣的選擇、意圖與道德情感,因為故事及論述正是說話者與聽眾彼此說服——而不是限制、評判——的工具,在故事及表述的過程中,道德可能性才逐漸顯現出來。廢死論述因而必須不斷傾聽人們的故事,廢死論述也要不斷擴展自己故事及表述的形式(非語言的形式),透過不斷挖掘與找尋擴展生命價值的故事,提供人們在死亡事件上的轉化機制。
當我們持續深化對這個「庶民」正義的認知和修正,可以回過頭來對法律人類學的假設和方法有所啟發,就像我在社區大學的論壇得到的經驗。那麼法律人類學能夠或應該在這場戰爭打前鋒嗎?死刑存廢的辯論可以從死巷裡活過來嗎?
編按:本文為芭樂小編擷取、編輯而成,作者原文請見:容邵武 2012,《 死刑戰爭:法律人類學的中介》,文化研究,14: 101-138。以及2012,《面對公眾的法律人類學》,人類學視界8。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容邵武 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來自法律人類學的觀察
編輯精選
